疫情下咨询师的工作面临的考验
我们面临的情况是似乎我们的世界突然暂停。
我们既不能思考它,也无法想象它,这导致的后果是在很多人那里会产生一种不知所措。
2020,对所有从事临床的心理咨询师都是一个考验,法国精神分析家卢梭先生上周日以“疫情期的临床工作”为主题,隔空对话中国的分析家们,中法分析家们面对疫情有很多共性的问题。
比如来访者的状态,来访者中焦虑、抑郁致增高的不在少数,而分析家面临的问题是无法在身体在场的情况下和他们工作,隔离使我们被迫选择网络或语音工作,这给分析的临床带来了困难和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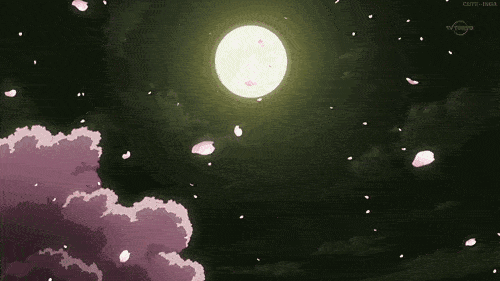
一.
疫情打乱了我们与时间的关系
居家封闭的政策拷问着人类个体存在的极端孤独,加剧了我们的苦恼,激活了一些精神的创伤,揭示了生活所强加给我们的不足和缺失,也动摇了我们的某些价值观,问询着我们的优先权,推动我们去质疑以前那些优先的东西。
居家封闭的处境在不同的个体那里导致了不同程度的被压抑之物的返回,或者更广泛意义上来说,所有令我们返回到早期经历的东西的返回,特别是感官接触的一种需要,他人物理身体在场的需要,这些需要是能够让我们安心下来,或者是抚慰我们的源泉。
在我们的来访者身上,由于缺少了一些人际间的交往,会导致一些情况的加重,导致一些非常深远的事物的重新泛起。很可能首先要处理的是在他们身上隐藏的内心小孩所面临的困境。所谓内心的小孩,已经被他所变成的成人(也就是我们)所遗忘,但他曾经需要被肯定,被支持,被包容。这是我们在来访者的抱怨中很容易听到的东西。
我们听到这个内在小孩被遗忘,这个遗忘的后果是它会请求一个全能的保护者,不管是母性还是父性;它有一个风险,这个小孩会呆在依赖的安逸的处境中不出来。
在目前的情境下,来访者很容易把我们放在一个导师或精神领袖的位置上,因此我们必须保持一种警惕,不要给出直接的、封闭的答案。
我们需要利用这些时间,以便来访者能够更好地自我理解,解除自我束缚和自我抑制,允许他们自己能够更多地靠近他们自己。大家知道弗洛伊德有《抑制、症状与焦虑》,是指抑制住一个东西。
对我们这些心理工作者来说:
帮助所有人去作出一种关于未知的想象或表象,可以通过一个具体的形象,以便能够建构起一个背景,在其中我们仍然可以重新成为自己生活的主角,而不仅仅是作为所有到来的事件的旁观者。
二.
焦虑的提升
无所不在的令人担忧与忧虑的信息的泛滥,导致一些症状的恶化。
大部分来访者,现在都是是非常焦虑的。这种担心和焦虑不仅仅是关于现在的病毒流行以及危险性,他们也焦虑接下来如何与流行病一起生活。
他们会自问“我如何能够从居家封闭的状态中走出来,重新回到之前的普通的生活呢?目前的灾难会产生什么样的经济的后果呢,代价是什么,谁来为代价负责。”
在这样一个居家封闭的阶段,对灾后生活的焦虑,加重了由隔离所强加的焦虑。
每一个人都等着分析家来让他们安心,帮他们的焦虑找到一个边界,很多人都害怕不能再从焦虑中走出来。
他们长时间向分析家展示他们生活的困难,要么是多个人在一起的混乱的生活,要么是相反,完全被世界遗弃,难以忍受隔离的孤独一人生活的状态。

考虑到疫情持续的打击,对未来的疫情之后的焦虑,以及可能要持续几个月的生活状态的焦虑,开始不断地侵袭他们。
由于症状,他们很难好好考虑未来的活动,包括职业生活和家庭生活。来访者很多时候怕的并不是病毒本身,他们恐惧的或焦虑的是居家封闭的状况。
焦虑的增高和增长经常表现在他们醒的时候,或者是当他们失眠的时候。
当然,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未来经济的前景是经常被他们提到的,在这个表面的背后,很容易听到他们世界的崩溃,或者是他们自身的崩溃,或者听到他们某种生的欲望的丧失,有一种自我的封闭,封闭在忧郁的思虑中出不来,以及他们在这时突然认识到面对死亡的脆弱性。
我们注意到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似乎有这么一个等式,疾病=死亡,在他们身上这个等式是非常坚定的,他们坚信这一点。
但是与我们后面要谈到的忧郁的状态不同,焦虑的人看到的是这样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在他们死后会继续存在,他们自己因为死亡而被排除在这个世界之外。
作为心理治疗师,我们必须能够倾听并接受他们的焦虑,不是以一种防御的方式去倾听他,特别的如果这些焦虑在我们身上也产生了同样的害怕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否认我们的来访者的话语的特殊性或者主体性,也不能混淆我们的主体性和他们的主体性,不要想走得太快。在任何情况下不应该涉及去教导或指导我们的来访者,而是允许他们自己去发现能够维系自己的东西。
在目前的情境下,努力地帮助来访者认识到这些焦虑之类的所有问题已经在那里了,在他们身上存在了很多时间,这些问题是合理的,并且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想法并不是糟糕的想法或者不恰当的想法。
尝试去帮助他们,发现在他们的焦虑之下掩盖着一系列的防御的机制。
正是围绕着这些防御的机制,组织或产生了不同的症状,包括恐惧症性的,抑郁症性的,强迫症性的(强迫性仪式),或者更进一步是癔症性的,正是我们与他处理这些所有症状的咨询工作让他们逐步离开让他们焦虑的真正源泉。
来访者需要能够逐步地与他们的过去分离,将他们的现在与幼儿期分离,否则他们会困在无休止的强迫重复性的痛苦中无法自拔。
所有的症状是为解决我们的心理冲突,我们知道它们都是一些妥协的表达。
心理治疗工作的一个目标是允许来访者认识、承认和接受他们身上的心理的冲突,以便能够重新发现一种潜在的运动性,而不是被他们的重复困在那里一动不动。
三.
精神病性的忧郁
首先强调精神病性的忧郁是在目前封闭的状况下,所遇到的非常重要的症状。
忧郁出现在主体与他的时间、空间、身体,语言的逐步损害之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去倾听他们所维持的关于这些主题的看法。我们要注意封闭在家的来访者是如何持有关于身体的含义,他们身体的运动的需要,移动(出门)的需要。
举一个例子,一个来访者被封闭在家里,他说整天待在家里,什么都不穿,不停地思考他被封闭的自我灭失。我将他的咨询时间调到很早,通过视频或电话的方式,以便处理他所展示的东西。我甚至同样也考虑在他的案例中,给与他一种多次数、短时间的咨询。
在第一个层级之下,我试图与他最古老的的自我进行工作。因为他最古老的最根本的自我是处在痛苦中的,我们需要将其重新自恋化,以及支持这样一个自我。
这个来访者很早就被他的单身母亲抛弃,这个母亲要工作,将这个孩子托付给孩子的外公外婆,但外公外婆酒精成瘾,并且非常暴力,也因为没有父亲,所以经常被蔑视并被取笑他的出生。结果导致来访者产生了持续的不安全感,试图养一些动物来减少这种不安全感。
和这个来访者,我们的工作会建立在当下的状况,他现在能找到的以及能建构的资源,很多时候都在坚持稳定他现在当下的生活。我试图阻挡他逃避到非常严重的自我贬低、自我摧毁的忧郁的思想中。
我也会围剿他认为什么都没有意义的信念,这是通过一个关于意义的工作来展开。
我试图鼓励他找到一些他生活中突然出现的潜在的可能,我试图对这些东西赋予新的价值,让他找到一些特别确定的东西。
但是他仍然在一个非常脆弱的状态下,目前事实上我更多的是起到一个支撑的功能,但支撑的功能被原来面对面的会见的中断所破坏。对这样一个以视频方式工作的来访者来说,尽管频率固定且次数非常多,但依然不够,我非常为他担心。
忧郁的状态不能够仅仅是从对一个丢失客体的哀悼的丧失的角度出发,而是也要考虑到有可能有一些可怕的暴力的客体闯入了精神建构之中。

在他们的精神建构中,可怕的东西的闯入,这在忧郁状态下是特别令人担忧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待这个世界就像看待某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会同他一起消失。
对我来说,能够超越这种忧郁状态的所有的方式,都要求自恋的重新制作,它是如何实现的呢,是通过长期的工作,以便允许纳入相异性。在这里,我们处于一种从封闭自恋的状态向大他者目光开放的自恋的状态的转变。
心理治疗师的介入,会作为一个外部的位置,更准确地说是在以持续的稳定的外部状态,这种状态能够改变自恋的朝向。在面对忧郁的情况下的工作,本质上是支撑在一个可能性上,这种可能性是主体将关于自身的想象的形象的进行转变,融入进大他者送给他的形象中。
由此,主体能够进入一个恒定的认同中,认同的是一个位于无意识场景中的具有保护功能的形象,是关于一些从一开始就对他而言是缺失的客体的痕迹。这是一个类似的保护性的工作,我们要重构一个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没能很好建构的客体。
四.
神经症状态的抑郁,抑郁症
抑郁的特点本质上是与关于生活意义的丧失有关,这样的丧失还伴随着生殖快乐的缺乏,会产生不同种类的次级表现或继发表现,比如说非常大非常深的疲乏,缺乏胃口,渴望的缺乏,愿望的缺乏,当然也有器质性的身体的障碍。
在目前的居家封闭的状态里面,事实上是封闭的状态在折磨来访者,而不是疾病的危险在折磨他。对那些比较脆弱的人来说,不能够出门构成了特别严重的束缚。他们惯例的生活被打断,社会性的约会都被取消,而后者的两样对他们来说是允许他们维持某种平衡的唯一的东西。
我们的倾听首先当然是一个帮助,但这个帮助首先并不是治疗的效果,而是让他们宽慰和轻松。正是通过我们对他们无条件的关注,无条件的接受,接受他们的抱怨,他们的恐惧,他们的痛苦,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才能够逐渐建立起真正的咨询和治疗。

那么我们的工作会介入他们现在的生活,让他们的苦恼,焦虑,抑郁的状态暂停下来。居家的政策相反是加剧了这样的状态。
举一个临床的例子,一个女老师,我们称她为M女士,从她辞掉她的工作以来,我们已经工作了好几个月。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使得她的状况正在改善中,我们可以开始寻找抑郁表现之下的部分隐藏的无意识源头。
英国精神分析家温尼科特通过他临床的工作,向我们展示早期母子关系的可能的失败,以及当母子关系建构糟糕的情况下,或严重或不严重的后果。比如说当母亲没有足够好的时候,没能很好的承担起对生的快乐的唤醒者的角色时。
术语“足够”是非常重要的,我要强调这个“足够”。我们不需要母亲是完美的。
母亲作为人的缺点有助于孩子发展出新的去向——就算孩子很小——发展潜在的可能性。孩子可以在他和母亲之外去寻找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在母子关系中感受到的缺乏的东西、缺失的东西,因为需要的满足会产生快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母亲如果是完美的母亲对孩子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她没有给孩子留下空间去发展可能性,去独立。
我回到我刚举的女老师的个案里。这个夫人被固定在一种尊重的丧失的痛苦中。尽管别人对她的不尊敬,在旁观者看来是很少的。我已经成功地使她逐渐放弃与她痛苦相连的快乐,而去转向另外一些关系,这些东西给她带来新的东西,特别是她的性生活。
在二月初的时候,这位夫人开始打算重新回到工作中。正在这个时候,法国开始采取了封闭的政策,导致学校关门,就又将她推入这种痛苦的麻木中了。
她甚至向我承认说用电话的分析、而不是现场的分析让她感到很轻松,这样她就不用出门了。这时她开始持续的抱怨:“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很无能,我对自己的生活都无能为力。”她也非常羞愧,总是感觉很羞愧,她不能去做在这个空闲时间她应该做的事。“我应该做”就是为了更好的自我攻击。
在这个封闭的状态里,给她带来压力的并不是缺乏朋友的联系、家人的联系,因为有好几个月之前她已经远离了这些。她感到心满意足的是她能重新开始对着我不知疲倦地说她的抱怨。她找到了一种享乐就是强迫我去接受所有她说的东西,或者把我们的治疗关系导向失败。
有意无意地让我们治疗工作的失败,实际是允许她恢复她掌握一切的全能感,以及通过我来清算她和母亲之意象。这样的状况对治疗师来说是挑战和考验,因为在他(治疗师)身上可能引起一个负向反转移。负转移产生后,治疗师就更有必要和督导一起治疗了。很幸运我没有产生这些负转移。
我的精神分析的工作是帮助她发现那些缺失、那些侵犯、那些创伤。我的来访者的自我的建构出现了偏差,和他们的工作允许我向他们展示这些东西,以及解释和阐明。我如何向她们表现、解释、阐明这些东西呢?这需要必要的柔性技术,每个治疗师都需要这样弹性的技术。
它涉及到的是发现那些束缚着来访者的精神建构的东西,当我们能假设说她们的母亲不是足够好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地方,围绕着精神的建构,以及围绕母性角色客体的建构会有一个工作。不是说仅有母亲这边,有的时候也需要强调父亲作为相异性客体的功能,这样父亲能帮助孩子去转向他。这是非常早的让孩子转向父亲。
这样的父亲也是把母亲不是作为全能的母亲,而是把其放到女人的位置。因为正是这样一个复杂性,它维持、允许主体健康自恋的建构,这样的建构是与性别、代际有关的。治疗的重点是对来访者的初级自恋进行重新工作。这样一个自恋是一个法国分析家Andre Green 称为”生活的自恋”,也是主体精神构造的基础。
这些生活的自恋允许我们对自己的生的快乐进行投注,并创造新的客体。这些客体能滋养我们的生活,以及给我们的生活以意义。
正是幼儿在他早期与母亲及母亲替代者所经验到的牢固的关系,是从这种感觉出发,我们会找到生活的意义。它们就涉及构造一种能力,在广大的意义上去投注周围的客体,甚至创造一些客体,并能够将提供给我们的东西价值化为有意义的情感。

文:金瑜
责任编辑:殷水
发布于: 2020-04-30
©️文章转载/侵权,请联系邮箱:content@xinli001.com









写的真好!共同成长
一如既往地喜欢